文化复兴中的价值取向重构当今世界,许多和地区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变革,为人类社会注入了活力与希望。在这场复兴中,重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关键环节。首先,我们需要

学问是“做”出来的。自觉地做学问,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小满未满,我感到有五对范畴值得认真地思考和深切地体会:一是名称与概念,不只是时令,二是观察与理论,更暗含自古以来的中庸智慧。“小满者,三是苦读与笨想,满而不损也,四是有理与讲理,满而不盈也,五是学问与境界。
名称与概念
黑格尔有句名言: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满而不溢也。”它是初夏时节的小欢喜,往往是最无知的。这是因为,是生活的小满足,人们用以指称和把握对象的任何一个名词,也是人生的小得到。意味着一切都还没有成定,都既可能是关于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来日方长,也可能是关于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名称只是一种熟知,万物可期。快来和记者一起,一种常识,概念则是一种真知,一种理论。熟知不需要专业性的研究,真知则需要专业性的研究。把熟知的名称升华为真知的概念,就是把非专业的常识上升为专业化的理论。因此,所谓专业地“做学问”,其实质内容就是把名称变为概念。
比如,非物理学专业的人,也总是使用声、光、电、分子、原子、微观粒子这些名词,但这些名词只是用以指称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而不是用以把握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同样,非哲学专业的人,也总是使用存在、物质、规律、真理这些名词,但这些名词同样只是用以指称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而不是用以把握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例如,究竟什么是“存在”?在用以指称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中,“存在”就是“有没有”,“有”就是存在,“没有”就是不存在。然而,在用以把握对象的规定性的哲学概念中,“存在”成为全哲学思想的聚焦点。从巴门尼德的存在与非存在到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界,从黑格尔的“纯存在”到马克思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存在”这个名词获得了历史性的和性的哲学内涵,从而构成积淀和结晶着全哲学史的哲学范畴。因此,在哲学专业的意义上使用“存在”这个概念,就必须是以“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去辨析这个概念,深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列宁说,概念、范畴并不是认识的工具,而是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这就是说,在人类认识的历史进程中,概念、范畴既是认识的积淀和结晶即认识的成果,又是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即认识的前提。作为认识的结果,它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专业化的研究成果;作为认识的前提,它直接地构成专业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前提。
概念、范畴作为专业化的认识的结果和前提,蕴含着相互依存的两方面内容:一是它积淀和结晶了人类的认识史,二是它内涵着“整个世界”和“全生活”。人类的认识史,既是对“整个世界”的规定性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认识,又是对“全生活”的意义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的理解;而对“整个世界”和“全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又构成人类的认识史。因此,真正把名称升华为概念,也就是从非专业的熟知升华为专业性的真知,就必须形成两个自觉意识:一是“寻找理论资源”,“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以概念作为专业性研究的“阶梯”和“支撑点”;二是把握本学科关于对象世界的规定性以及本学科已有的对“全生活”的理解。从名称到概念,这是专业地“做学问”的基本前提。
对于“做哲学”来说,要把名称升华为概念,“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与对“全生活”的体悟和思辨,是同等重要的。首先,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离开思想性的历史,就无法形成历史性的思想。哲学从名称到概念,就是在思想性的历史中不断地结晶为历史性的思想。不熟悉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名词就只能是常识性的名称,而不可能是哲学概念。其次,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历史性的思想只能是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对生活的体悟和思辨的产物。历代的哲学家都既是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又是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生活的意义。理解他们对生活的理解,特别是超越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就必须注入我们的体悟和思辨。否则,我们所接受的就是没有生命的名称,而不是活生生的概念。学和研究哲学,慎思明辨的理性和体会真切的情感,是不可或缺的。黑格尔说,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那里,与在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子那里,其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辛弃疾说,同一个“愁”字,少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老人则是“却道天凉好个秋”。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观察与理论
概念、范畴作为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它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直接地表现在它是阅读文本和观察现实的理论前提。由此就提出“做学问”中的观察与理论的关系。
人是历史、文化的存在,人们对文本的阅读和对现实的观察,必须并且只能以已有的概念、范畴、知识、理论构成基本的主体条件。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说法就是: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借用黑格尔的说法就是:没有概念把握的对象,对象只能是“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对象存在着,但对认识的主体来说并不存在。生活中的简单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体检时的胸透片和心电图,被体检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医学知识,虽然胸透片和心电图放在眼前,但却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肺和心脏是否有毛病。同样,如果没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地质的或天文的相关知识,各种的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地质现象或天文现象,对观察主体来说也是“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
这个常识性的道理,对于“做学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理论既是把握和解释观察对象的概念系统,又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概念系统。首先,理论具有解释功能。它的概念系统凝结着人类的认识史,结晶着人类对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因而能够对事物即观察对象做出超越经验性描述的规律性的解释。离开理论的观察,只能是对观察对象的经验性的描述,也就是把名词当做指称对象的名称。其次,理论具有规范功能。它以自己的概念系统规范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也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行为内容和行为方式,即规范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离开理论的观察,就难以在问题的意义上去想什么和做什么,更不知道应当怎样想和怎样做。许多人之所以提不出真实的问题,理解不了真实的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应有的理论。再次,理论具有批判功能。它以自己的概念系统审视和反人的思想和行为,质疑和矫正人的思想和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正是理论的批判功能,才能引导做学问的人发现理论困难和创新理论思路。离开理论的批判,既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更难以做出有说服力的批判。一些“质疑”或“商榷”文章之所以言不及义或难以服人,其重要原因也在于缺乏相应的理论。最后,理论具有引导功能。理论是构成目的性要求和理想性图景的深层根据,它的概念系统引导人们认同新的价值目标和世界图景。因此,有没有阅读文本和观察现实的相应的概念系统,有多少和什么样的参照的概念系统,直接地决定“做学问”的层次和水平。
苦读与笨想
做学问必须“读”和“想”,但仅仅是“读”和“想”,对于做学问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地做学问,必须是“苦读”和“笨想”。
做学问需要两个积累:一是文献积累,了解和熟悉别人的相关的研究成果,“得道于心”;二是思想积累,形成和论证自己的独到见解,“发明于心”。前者主要是“寻找理论资源”,后者则重在“发现理论困难”。前者需要“苦读”,后者需要“笨想”。
所谓“苦读”,强调的是一个“苦”字——不一目十行,不浮光掠影,不寻章摘句,不只过目而不过脑。首先要知道人家到底说些什么,人家到底怎样论证自己的说法,人家的这些说法到底有什么根据和意义。总之,读书首先要“发现人家的好处”。如果发现不了人家的好处,概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因为它确无价值,或者是因为自己没读进去。如果是前者,可以由此引发自己对问题的思考;如果是后者,那么书就等于白读了。读进去,读出人家的好处,才能成为自己的理论资源,才是“得道于心”。
“读”,又不只是为了“寻找理论资源”,而且是为了“发现理论困难”。这不只是说要发现阅读对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发现阅读对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他所面对的真实的理论困难是什么。借用王国维的读书三境界,读书首先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博览群书,开拓心胸和视野,修炼性情和品位;其次是“衣带渐宽终不悔”,钻研问题,呕心沥血,磨炼意志和毅力,施展体悟和思辨;第三境界则是“众里寻它,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别人未见之处找到真实的问题。要达到第三境界,仅仅“苦读”又不够了,还必须“笨想”。
所谓“笨想”,强调的是一个“笨”字——不投机取巧,不人云亦云,不耍小聪明,抛开一切文本,“悬置”一切成说,面向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种“笨想”中,“人云”的一切都化为退入背景的知识,都不再是“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乃至“笨”到只是追问谁都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通常都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化的世界观”,然而,究竟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还是人在世界之中“思”世界?具体言之,什么是世界观的“世”?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然的“世”,还是人生在世之“世”?什么是世界观的“界”?是与人无关的无始无终的“界”,还是人在途中之“界”?什么是世界观的“观”?是与人无关的物的目光和神的目光,还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对世界观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发现关于世界观的不同的解释原则,才会发现各种哲学的根本分歧。只有“笨”到追问各种似乎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毋庸置疑和天经地义的问题,才会形成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
“笨想”是以“钻进去”的“苦读”为基础,以超越“苦读”的“跳出来”为目的的。不以“苦读”为基础,所谓“笨想”就只能是没有根据的突发怪想或胡思乱想,要么什么也想不出来,要么想出来的没有意义。但是,如果只是“钻进去”的“苦读”,也难以形成“跳出来”的“思想”。这就要求做学问必须有两个积累:一个是“苦读”所形成的“文献积累”,一个是“笨想”所形成的“思想积累”。没有扎实的“文献积累”,就不会形成真实的“思想积累”;仅仅有“文献积累”,却不一定能形成真实的“思想积累”。借用形式逻辑的道理,这就是:“苦读”及其所形成的“文献积累”,只是形成思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形成思想的充分条件;形成思想的充分条件是复杂的,除了文献积累之外,至少还必须加上由“笨想”所形成的思想积累。思想积累多了,就形成了自己的有系统的思想。
有理与讲理
苦读和笨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理”——不仅想清楚别人所讲的道理,而且想清楚别人没讲的道理。想明白的道理就是学问,想明白道理的过程就是做学问。做学问就是在苦读和笨想的过程中想清楚别人讲过的、特别是别人没讲过的道理。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别人所讲的道理,自己是否真的明白了?特别是别人没讲的道理,自己是否真的清楚了?或者说,自己觉得“有理”,是否真有道理?这就需要“讲理”——把自认为清楚和明白的道理讲出来、写出来,让它们成为自己和他人的批判对象,看看这些道理是否经得起追问、经得起质疑、经得起推敲。我把这个“讲理”的过程,称做“基本理念概念化”的过程,也就是对自以为清楚的道理进行系统性的论证和辩证的过程。这个“讲理”的过程,同“有理”的过程是同等重要的。
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全体的自由性”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环节的必然性”,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虚幻的、抽象的、空洞的“自由性”,因而只是一种“意见”,而不是“真理”;二是体现为、实现为“环节的必然性”的“全体的自由性”,因而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具体的、丰富的“自由性”,因而不只是一种“意见”,而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理性具体”。所谓“做”学问,即把学问“做”出来,就是要把“基本理念概念化”,要在“讲理”的过程中达到“理性具体”。黑格尔说哲学是最具体的,是最反对抽象的,就是要求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为“环节的必然性”,把无规定性的名称升华为规定性越来越丰富的概念。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其基本理念概念化的理性具体,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其基本理念概念化的理性具体。《逻辑学》为我们讲述了黑格尔的思想的内涵逻辑,《资本论》则为我们讲述了马克思的历史的内涵逻辑。这两经典著作,都为我们提供了“讲理”的典范、“做学问”的典范。
“有理”是把道理“想清楚”,关键在于“苦读”和“笨想”;“讲理”是把道理“讲明白”,关键在于“分析”和“论证”。而是否真的“想清楚”了,又在于是否真的“讲明白”了。所以,“讲理”不只是把“有理”系统化、逻辑化,而且是把“有理”引向清晰、确定和深化。因此,“讲理”不只是要“说”明白,更要“写”明白。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写”是比“说”更重要的“讲”。
把“讲”当成“说”,往往会避重就轻,避难就易,轻描淡写,“化险为夷”,能说的就说,说不通的就滑过去。其结果,那个“全体的自由性”并没有实现为“环节的必然性”,那个“基本理念”并没有“概念化”,因此,那个“基本理念”或“全体的自由性”是否真的“有理”,也就不得而知了。
把“讲”作为“写”,情况就不一样了。“写”就必须把“基本理念概念化”,必须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为“环节的必然性”。这就是论证和辩证。在论证和辩证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名词”都不能只是一个指称对象的“名称”,而必须是一个关于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只是孤立的观念,而必须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中获得相互的规定和自我的规定、相互的理解和自我的理解;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只是抽象的规定,而是在由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中获得越来越丰富的规定,并由此构成“环节的必然性”。所谓辩证法,就是在概念的相互规定中达到理性的具体。马克思说,人们可以对《资本论》提出各种批评,但《资本论》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他是引为自豪的。作为“完整的艺术品”的《资本论》,就是运用辩证法的艺术,就是在“讲理”的过程中所实现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思想者是以思想为生的。用“痛并且快乐着”来形容学者的生活,概是最恰当的。这个“痛并且快乐着”,不只是体现在“苦读”和“笨想”的过程中,而且更深切地体现在“讲理”即“写作”的过程中。许多人之所以不能“读”出“人家的好处”,之所以不能“想”出“自家的道理”,关键在于不能“写”出“自己的文章”。事非经过不知难。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红楼梦》是把生活的山推倒,又重塑了艺术化的生活的山。学问家也是把观念的山推倒,又重塑了理论化的思想的山。“写”出“自己的文章”,是以苦读和笨想为基础的“讲理”的过程,是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为“环节的必然性”的过程,真正“讲理”的“专著”是“痛并且快乐着”的产物。许多的书籍之所以只能称之为“编著”,而不能称之为“专著”,就在于它的产生并没有真实的“痛并且快乐着”的过程,因而也就没有实现“基本理念概念化”,也就是没有实现“环节的必然性”。
“讲理”是艰苦的。“讲理”的过程,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过程。作为人文学者,“讲理”有三个要素:一是思想,二是逻辑,三是语言。所谓“思想”,就是要有独立的创见,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讲出别人没想到或没想清楚的道理;所谓“逻辑”,就是要有严谨的论证和睿智的辩证,这就需要“在论证上跟自己过不去”,讲出“环节的必然性”;所谓“语言”,就是要有清晰而优美的表达,这就需要“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把道理讲明白、讲透彻。“有理”和“讲理”是艰苦而又快乐的创作过程,也就是“做学问”的学者的生活。
学问与境界
人们常把“为学与为人, 其道一也”视为做学问的至理名言。然而, 人们对于这个“道”的理解并不一样。我觉得, 为人之道和为学之道, 都是达到一种“洒脱通达的境界”, 因此“其道一也”。
为人和为学的“境界”, 并不是玄虚的、神秘的, 它具体地体现在为人和为学的“气”、“正气”和“勇气”之中。所谓“气”, 就是“立乎其者”, 有高尚的品格和品位, 有高远的志向和追求, 有高明的思想和见地;所谓“正气”, 就是“真诚地求索”, 有“抑制不住的渴望”, 有“直面事情本身”的态度;所谓“勇气”, 就是“异常地思考”, 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念, 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理想。这种“气”、“正气”和“勇气”, 就是为人、为学的“境界”。
气, 首先是志存高远,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有博的人文情怀, 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博的人文情怀去捕捉和发现时代性的重问题, 并以理论的方式直面现实, 这是思想者的最为根本的气。气又是“先立乎其者”。海德格尔说, “事物的开端总是的”。对于“做学问”来说, 开端的, 就是在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形成自己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它是照亮自己所研究的全问题的“普照光”。一个搞哲学的人, 没有对哲学本身的深切的追问, 没有关于哲学的真切的体悟, 是难以达到哲学“境界”的。例如, 把“哲学”分解为若干二级学科进行专门研究是必要的, 但是, 没有超越各个二级学科的哲学理念, 却往往导致并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提出和论证问题, 乃至出现哲学常识化或哲学科学化的思潮。再如, 把“哲学”研究具体化为对哲学家、哲学论著、哲学派别、哲学思潮的研究是重要的, 然而, 没有研究者自己对哲学本身的总体性理解, 没有研究者自己对哲学基础理论的系统性把握, 既难以真切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思想, 更难以真实地提出超越研究对象的思想。研究者的学养、悟性和境界, 深层地决定“做学问”的水平。
正气, 就是真诚地求索。“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自己有多少“文献积累”, 自己有多少“思想积累”, 自己有多少“独立见解”, 自己是最清楚的。讲课时, 什么时候理直气壮, 什么时候惴惴不安;写稿时, 什么地方酣畅淋漓, 什么地方捉襟见肘;这些, 有谁会比自己体会更深呢?叶秀山先生在《读那些有读头的书》一文中说, 你对老黑格尔提问, 可以一直追问下去, 他总有话对你说。我们的讲稿或论著, 究竟能够回答多少追问, 自己是清楚的。学问是老老实实的东西, 做学问需要老老实实的态度。这就是做学问的“正气”, 也就是做学问的境界。
勇气, 就是异常地思, 辩证地思,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于哲学来说, 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 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思维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 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 因此, “做哲学”就是“对假设质疑, 向前提挑战”, 追究生活信念的前提, 质疑经验常识的根据, 反思历史进步的尺度, 拷问评价真善美的标准, 反对人们对流行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念、审美情趣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这种异常之思, 植根于长期的“苦读”和“笨想”, 体现在切实的“有理”和“讲理”, 因而实现为富有启发性和性的思想。学问的境界, 就是有价值的思想。
《孙正聿讲演录》
长春出版社2011年出版
(本文源自《孙正聿讲演录》,长春出版社授权发布)
编辑:刘岩
IT百科:
爱疯系统内存怎么清理 vava硬盘怎么样 windows 10闪光怎么调
网者头条:
尤德民字画多少钱一平尺 翡翠怎么戴都好看吗女生 玉石画颜色怎么调色快一点 猫咪冬天为什么会叫出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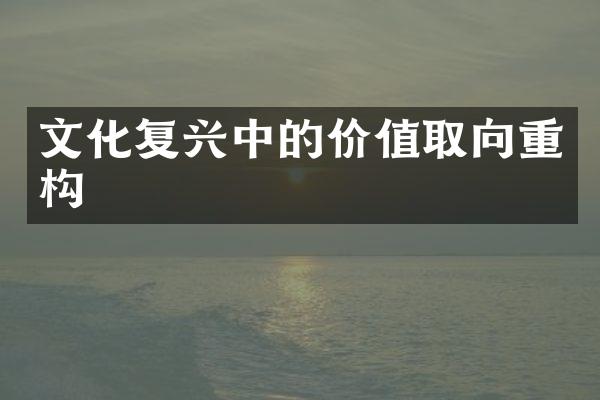
 1
1